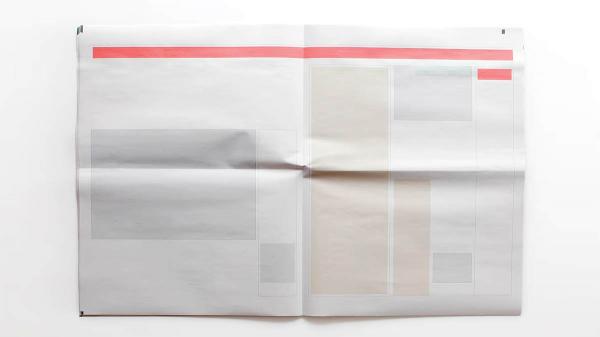風險管理 地緣政治加劇,高盛合夥人給企業 5 個求生錦囊
地緣政治加劇,高盛合夥人給企業 5 個求生錦囊
5 Rules for Companies Navigating Geopolitical Volatility
- 風險管理
- 傑拉德.柯翰 Jared Cohen
- 2025/02/04

nesneJkraM/Getty Images
在這個世界秩序愈發混亂的世界裡,企業不再只能專注於內部管理或市場競爭,尤其是台灣企業,更要學會如何在全球局勢中找到生存與成長的空間。高盛公司合夥人試著帶領導人思考五個關鍵問題:你的企業在全球舞台上有一席之地嗎?你懂得把握「搖擺市場」的機會嗎?你是否會把各個危機劃分開來思考?你知道針對轉折點做規畫嗎?你是否過度相信商業力量可以解決一切?
地緣政治是一門不確定的生意。大部分企業領導人曾經習慣的世界秩序,現在正面臨冷戰(甚至是二戰)以來最大的挑戰。歐洲與中東的戰爭,以及印度—太平洋地區日益緊張的局勢,使得世界變得更加動盪、更難預測。愈來愈像可能威脅全球安全與成長的地緣政治情勢急轉直下,少有化解之道。
執行長與董事會在一個更加動盪的世界中前行,因此他們最常用的詞是「風險」。他們的員工、營運作業、股東與其他利害關係人面臨什麼風險?他們如何去除供應鏈的風險?從傳染病到網路攻擊到戰爭,有哪些風險他們還沒想到,或尚未準備好應對?
在過去10年,我們透過更具挑戰性的地緣政治新現實,看到新的企業領導模式。這些模式遵循5條法則,適用於尋求調整適應、創新與成長的企業,即使在維持全球和平與安全的「美國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正在受到考驗,需要嚴肅對待的領導人來維持的地緣經濟環境中,仍然適用。
1. 尋找一席之地與機會來塑造你的角色
讓全球經濟以歷史性規模成長的自由企業制度,仰賴規則與制度。但是這些規則與制度也是由權力來執行與維護,特別是那些有意願使用這權力的民主國家,也就是美國及其盟友與合作伙伴。
然而,在各國政府保護全球商業的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