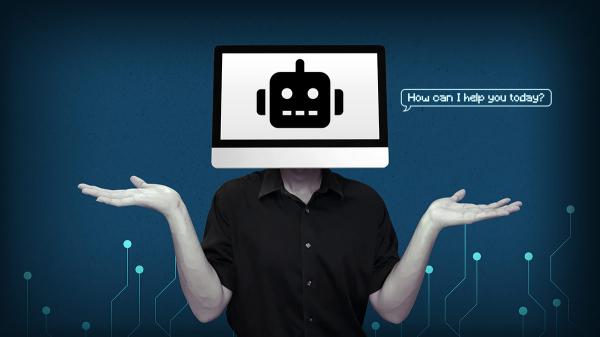經濟循環與趨勢 面對刻意製造的不確定性,我們需要「策略可選擇性」
面對刻意製造的不確定性,我們需要「策略可選擇性」
Navigating the Economy Amid Deliberate Policy Uncertainty

Klaus Vedfelt/Getty Images
川普曾表示:「我喜歡讓人無法預測。」當經濟政策變來變去,貿易條件朝令夕改,誰都很難預測下一步會發生什麼。面對這種「刻意製造的不確定性」,企業與其咬牙苦戰,不如學會一種更靈活的應對方式:「策略可選擇性」(Strategic Optionality),意即,你不必一次押上全部籌碼,而是設法打造多種選項,讓自己無論面對哪種政策組合,都還有應變的餘地。
消費者情緒低迷、金融市場不穩定,以及四處出現令人失望的總體經濟數據,這些都引發人們擔憂美國經濟衰退。福斯新聞(Fox News)的瑪麗亞.巴蒂羅姆(Maria Bartiromo)最近問川普總統,是否預期今年會出現經濟衰退,他也說「討厭預測這樣的事情」,並沒有反駁之意。
目前沒有任何證據顯示,自川普總統接掌政權8週以來,美國經濟的基本面已經突然惡化。真正改變的是,白宮刻意引入政策變化的不確定性,當成一種政治策略。川普曾經寫道:「我不想讓人知道我究竟在做什麼,或者在想什麼。我喜歡讓人無法預測。」
所有這些都表示,目前企業高階主管面對的情勢裡,風險上升、能見度下降。川普刻意製造的不確定性,增添了新風險,但是當前的經濟擴張是否已經寫下句點,並不像輿論喜歡描繪的那樣明確。
風險上升,但經濟還沒走到末路
關稅——何時實施、適用範圍、稅率高低,以及維持或調升的程度——對美國經濟構成相當大的風險。關稅是對外國生產商課稅,會加重進口貨的成本,而在大多數情況下,這些成本會轉嫁給消費者。
關稅的適用範圍和持續時間長短的不確定性,引發通貨膨脹再起的疑慮。他在2018年實施的關稅,當時正值通膨偏低,只造成物價一次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