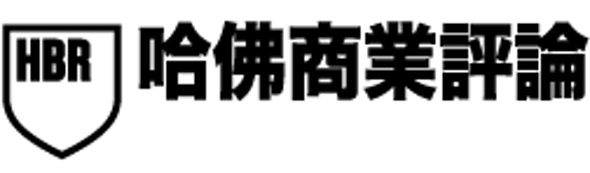經濟學與社會勞動階級「絕望死」,哈佛教授:正視傷害、重塑工作尊嚴
勞動階級「絕望死」,哈佛教授:正視傷害、重塑工作尊嚴
- 經濟學與社會
- HBR好讀 HBR CC Book Digest
- 2021/05/18

Ksenia Chernaya / Pexels
政府有責任打造經濟與社會機制,使個人能以其自由與工作尊嚴受尊重的方式貢獻社會。
從二戰結束一直到1970年代,沒有大專文憑的美國人還是可以找到好工作,養家活口,過上舒服的中產階級生活,如今卻困難許多。過去40年,大專和高中畢業生的所得差距(也就是經濟學家所謂的「大專溢酬」)增加了整整一倍。1979年,大專學歷者的所得比高中學歷者高出40%,到了2000年代已經變為80%。
全球化帶給高學歷者豐厚的報償,卻對大多數一般勞工毫無幫助。從1979至2016年,美國製造業工作數從1950萬個減少到1200萬個。生產力雖然提高了,勞工從自己生產所得裡分到的份額卻愈來愈小,大部分都到了執行長和股東手上。1970年代晚期,美國各大公司執行長的所得是一般勞工的30倍,2014年已經增加到300倍。
美國男性實質所得中位數已經50年停滯不前。儘管人均所得自1979年來成長了85%,沒上四年制大專的白人男性實質所得卻比過去還低。
工作尊嚴不再
可想而知,這群勞工並不開心,但經濟困境不是他們唯一的煩惱。才德至上時代還對勞動者造成了另一個更幽微的傷害,那就是削弱了他們的工作尊嚴。由於「頭腦好」才能在大學入學測驗考高分,導致篩選機制輕視學歷不高的人。這套機制告訴勞工,他們的工作在市場上比高薪專業階級的工作沒有價值,對共善貢獻較低,因此較不值得社會給予認可與尊嚴。這套機制正當化了市場給予勝出者的豐厚報償及不具大專學歷者的微薄薪資。
這套「誰配得什麼」的想法在道德上完全站不住,將工作的市場價值視為它對共善的貢獻度是錯的。然而,過去幾十年來,「收入反映一個人對社會的貢獻大小」的想法卻愈來愈根深柢固,在大眾文化裡隨處可見。
才德篩選機制更鞏固了這套想法,而1980年代以降各大中間偏右和中間偏左政黨擁抱新自由主義市場導向的全球化也是幫兇。儘管全球化造成了嚴重的不平等,才德思想和新自由主義世界觀還是削弱了反對全球化的立論基礎,打擊工作尊嚴,引發了對菁英的不滿與政治反撲。
2016年以來,名嘴和學者就不斷爭論這股民粹不滿的來源。是失業和薪水凍漲的關係,還是文化錯位的緣故?然而,問題其實無法這樣截然二分,因為工作既是經濟的,也是文化的;既是一個人的謀生方式,也是社會認可與尊嚴的來源。
這就是全球化造成的不平等會引發如此憤怒與不滿的原因。那些落隊者不僅看著自己苦苦掙扎,別人吃香喝辣,還感覺到自己的工作不再能換來社會尊嚴。在社會眼中,甚至是他們自己的眼中,其勞動付出都不再是對共善的寶貴貢獻。
不具大專學歷的美國藍領男性投給川普的比例極高。他們深受川普訴諸不滿與怨憤的政治語言吸引,顯示令他們苦惱的不是只有經濟困境。川普當選前那些年愈來愈明顯的徒勞感也反映了這一點。隨著學歷不高者的工作環境日益嚴峻,愈來愈多就業年齡男性甚至完全退出了勞動市場。
1971年,美國有93%的勞動階級白人男性就業,到了2016年只剩下80%,且無業的20%只有少部分人在找工作,感覺就像勞動市場不在乎他們的工作技能,讓他們備感屈辱,於是乾脆放棄。沒上大學者放棄工作的現象尤其明顯。2017年,美國高中以下學歷者只有68%的比例就業。
勞動階級甚至放棄生命:絕望死
然而,放棄工作還不是消沉的美國勞動階級最不幸的反應,許多人甚至放棄了生命,其中最可悲的徵兆莫過於「絕望死」(death of despair)的增加。絕望死是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安.凱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自創的詞彙。兩人近來發現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20世紀醫療進步減低了疾病的威脅,預期壽命穩定提高;但在2014至2017年,美國人的預期壽命非但沒有提高,反而開始減少,百年來首度連3年下降。
凱斯和迪頓發現,死亡率回升不是因為醫療科學不再發現新的藥物與療法,而是藥物過量、自殺與酒精性肝病致死的案例開始流行。他們會用「絕望死」來稱呼,是因為這些死亡都是自我造成的。這類死亡十幾年來數目不斷攀升,其中又以中年白人居多。1990至2017年,45歲至54歲白人男性與女性的絕望死人數增加了3倍;到了2014年,死於藥物、酒精和自殺的人數更首度超越了死於心血管疾病的人數。
生活在勞動階級活動範圍外的人起先對此幾乎一無所知,且由於媒體不關注而不曉得問題的規模與嚴重性。但到了2016年,美國每年死於藥物過量者已經比死於越戰的總人數還多。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尼可拉斯.克里斯托夫(Nicholas Kristof)所舉的對比更駭人:美國目前「每兩週」死於絕望死的人數比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18年殉難的人還多。
這場可悲的流行病從何而來?其中線索就在絕望死最好發族群的教育背景裡。凱斯和迪頓發現,「絕望死比例提高的族群幾乎都是高中以下學歷;四年制大專畢業者很少絕望死,風險最高的是沒有大專學歷的人」。
過去20年來,美國(45至54歲)中年白人的死亡率幾乎不變,但教育程度對死亡率的影響極大。1990年代以來,美國大專以上學歷者的死亡率降低了40%,高中以下學歷者卻提高了25%。這又是高學歷者的另一個優勢。只要擁有大專學歷,中年死亡的風險就只有高中以下學歷者的1/4。
兩者的差距主要來自絕望死。教育程度較低者死於酒精、藥物或自殺的風險向來高於大專以上學歷者,但死亡率的學歷落差愈來愈明顯。2017年時,高中以下學歷者絕望死的機率是大專以上學歷者的3倍。
或許有人會想,絕望死是因為貧窮造成的不快樂,會出現學歷落差只是由於教育程度較低者通常比較可能貧窮。凱斯和迪頓考慮過這一點,但發現證據不足。1999至2017年絕望死人數大幅上揚,和貧困人口的增加幅度並不一致。他們還逐州檢視數據,發現自殺、酒精和藥物過量致死人數與貧困人口增加並沒有明確關聯。
引發絕望的不光是物質剝奪,還和他們缺乏才德至上社會推崇獎勵的學歷以致於處處受挫有關。凱斯和迪頓做出結論,絕望死「反映了低學歷勞動階級白人的生活方式的慢性瓦解」。
擁有和不具大專學歷者差距愈來愈大,不只包括死亡方式,還有生活品質。高中以下學歷者的疼痛、疾病與嚴重精神痛苦指數持續攀升,工作與社交能力不斷下滑。差距擴大的還有所得、家庭穩定及社群。四年制大專文憑成為社會地位的「唯一」指標,感覺就像所有非大專學歷者都必須貼上紅字標籤,標籤上的「大學生」三個字用一條紅線劃掉一樣。
重建工作尊嚴
近年由於不平等日益擴大,勞動階級的不滿持續高漲,不少政治人物開始呼籲找回工作尊嚴。柯林頓提到工作尊嚴的次數比美國歷任總統都多,川普也常掛在嘴邊。工作尊嚴已經成為跨政治意識形態的熱門口號,只不過多半還是為了舊有的政治立場服務。
部分保守派主張削減福利,讓怠惰者難以偷懶靠政府過活,就能恢復工作尊嚴。川普政府的農業部長就主張,減少食物券可以「協助為數可觀的同胞重拾工作尊嚴」。2017年,川普為主要偏袒有錢階級的企業減稅法案辯護,宣稱法案的目的是「讓所有美國人知道什麼是工作尊嚴和領薪水的驕傲」。
自由派有時也會以工作尊嚴為由要求加強安全網,提高勞動階級的購買力,例如提高最低薪資,規畫健保、家事假與育兒政策,為低所得家庭減稅等等。然而,這套說詞即使有具體政策提案支持,卻未能撫平勞動階級的憤怒與不滿,最終導致2016年川普當選。不少自由派對此百思不解。這些選民裡明明有許多人的經濟條件能從這些措施得益,卻把票投給反對這些措施的人?
一個常見的回答是,勞動階級白人選民受文化錯位的恐懼影響,以致於就算經濟利益受損,也要像某些名嘴說的「用中指投票」。但這個解釋跳得太快,將經濟利益和文化地位視為截然二分的選項。經濟考量不只涉及口袋裡有多少錢,還涉及一個人的經濟條件如何影響其社會地位。對那些因為40年全球化與不平等而落隊的人來說,他們所受的打擊不只是薪資停滯,還擔心自己愈來愈邊緣,他們所在的社會似乎不再需要他們擁有的技能。
1968年尋求民主黨提名參選總統的羅伯特.甘迺迪參議員深知這一點。失業之苦不只在於沒有收入,還在於失去工作將剝奪一個人為共善做出貢獻的機會。「失業代表無事可做,代表跟我們所有人不再有任何關聯,」甘迺迪參議員解釋道,「失去工作,失去對同胞的用處,就等於成為作家拉爾夫.艾里森(Ralph Ellison)筆下的看不見的人。」
甘迺迪參議員當年察覺到的那份不滿,現在的自由派卻沒看見。他們不停提供勞工和中產階級更多的分配正義,更公平全面的經濟成長果實,但這些選民要的卻是更多的貢獻正義,一個提供別人需要與重視的事物以贏得社會認可與尊嚴的機會。
自由派強調分配正義,對一味追求國內生產毛額增長而言是很好的制衡。這樣的做法源自以下信念:一個公正的社會不僅追求更大的整體繁榮,還追求所得與財富的公平分配。依據這個觀點,任何目的在提高國內生產毛額或鼓勵產業將勞動力外包至低薪國家的政策,例如自由貿易協議,都必須在贏家補償輸家的前提下才值得考慮。譬如因全球化獲益的公司及個人必須繳稅,貢獻部分利潤加強社會安全網,提供失業勞工所得支持或職業訓練。
這便是1980年代以來,歐美主要中間偏左(及部分中間偏右)政黨的想法:擁抱全球化和全球化帶來的經濟發達,再運用所得的獲益來補救本國勞工因全球化遭受的損失。然而,民粹反撲等於宣告這套做法沒人愛。事後檢視殘局,我們不難看出這套做法為何失敗。
首先,這套做法從來沒有徹底實踐過。經濟確實發達了,但贏家並未補償輸家;不僅如此,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反而加大了不平等。經濟成長的果實幾乎全數流向了上層,勞動階級不是分得極少,就是一無所獲,政府徵稅也不見改善。由於政治愈來愈受到金錢左右,民主機制成為所謂的「寡頭遊戲」,造成重分配半途而廢。
然而,問題還不止於此。一味追求國內生產毛額,就算輔以對落隊者的補償,也等於將重點擺在消費,而非生產。這導致我們往往以消費者而非生產者的角度看待自己。實際上我們兩者皆是。作為消費者,我們希望錢的效用愈大愈好,產品與服務的價格愈便宜愈好,是海外血汗工人或美國高薪勞工製造或提供的都無所謂。但作為生產者,我們希望自己的工作令人滿足又有不錯的報償。
調和這兩種身分是政治的工作。然而,全球化只求經濟成長極大化,代表消費者利益至上,因此極少在意外包、移民和經濟金融化對生產者福祉的衝擊。一手主導全球化的菁英不僅未能化解全球化帶來的不平等,更沒看出全球化侵害了工作尊嚴。
工作即認可
不論提高勞工和中產階級的購買力或加強安全網,這些彌補不平等的政策提案都很難化解累積已久的氣憤與不滿,因為怨憤來自社會認可與尊嚴的消失。購買力下滑當然要緊,但讓勞動階級不滿的主要理由是他們的生產者地位被傷害了,而這是才德篩選機制和市場導向全球化造成的後果。
唯有正視這份傷害、重塑工作尊嚴,這樣的政治綱領才能確實化解造成目前政治動盪的不滿。這套綱領不僅要處理分配正義,也要關切貢獻正義,因為瀰漫在我們國內的這股怨憤至少部分源自認可不足。認可不是出自我們身為消費者,而是作為生產者對共善做出貢獻,進而贏得認可。
從消費者或生產者角色出發,會得到兩種看待共善的角度。第一種是許多經濟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將共善定義為個體偏好與利益的集合。依據這個觀點,共善就是消費者利益極大化,通常是靠極力追求經濟成長來實現。若共善只是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市場提供的薪酬就足以反映某人對社會貢獻為何。所得最高者提供消費者想要的產品與服務,對共善的貢獻也最大。
第二種角度反對用消費者定義共善,主張從公民立場出發。根據這個觀點,共善不僅僅是個體偏好的集合或消費者利益極大化,而是批判反省自己的偏好,甚至加以提升與改進,以活出充實豐富的一生。這個理想無法光靠經濟活動來達成,而是需要和其他人一起深刻思考如何造就公正良善的社會,培養公民德性,共同憑藉理性找出值得我們這個政治群體追求的目的。
因此,若想實踐公民角度的共善,就需要政治制度的配合,提供公共審議的管道與機會。此外,我們還需要換個方式思考工作。從公民的角度想,一個人最重要的經濟角色不是消費者,而是生產者。因為我們是以生產者的身分發展和發揮自己的能力,提供產品或服務滿足他人的需求,進而贏得社會尊嚴。我們做出的貢獻,其真正價值不能用薪資衡量,因為誠如經濟哲學家法蘭克.奈特所言,薪資取決於變動不居的供需。我們做出的貢獻,其價值來自我們所服務的目的,來自其在道德與公民層面的重要性。這需要獨立的道德判斷,再有效率的勞動市場都無法提供。
經濟政策的最終目的是消費,如今這個想法太過普遍,以致很難跳脫。「消費是所有生產的唯一目的與用途,」亞當.斯密在《國富論》表示,「唯有當顧及生產者利益才能促進消費者利益時,才需要照顧生產者利益。」凱因斯呼應亞當.斯密,主張消費是「所有經濟活動的唯一目的與終點」,絕大多數當代經濟學家也都會同意。然而,更久之前的道德與政治傳統卻不作此想。亞里斯多德主張人的滿全來自培養與發揮我們的能力,實現本性。美國共和黨的傳統信念則認為某些職業(最早是農業,其後是工藝,最後是各種自由勞動)能培養公民自治的德性。
20世紀以後,共和黨的生產者倫理逐漸消逝,被消費主義自由觀及成長導向的政治經濟路線所取代。然而,工作作為貢獻他人與相互認可的體制,能將所有公民連結在一起,再複雜的社會也不例外。這樣的想法並未完全消失,而是不時以發人深省的話語出現。金恩博士遇刺前不久,在田納西州曼菲斯市向罷工的清潔工人講話,就將清潔工人的工作尊嚴與他們對共善的貢獻連結在一起:
我們的社會終有一天會尊敬清潔工人。因為歸根究柢,社會要生存下去,收垃圾的人就和醫師一樣重要。他不收垃圾,疾病便會四處蔓延。所有工作都有尊嚴。
1981年,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通諭〈論人的工作〉裡表示,人藉著工作「滿全了自己的人性,甚至『更像個人』」。他還認為工作與社會不可分,「人將自己最深刻的人性與國民的身分合而為一,設法使自己的工作也能與同胞一齊促進共善。」
幾年後,美國天主教主教會發出牧函,闡述教會對經濟的社會訓導,明確定義了何謂「貢獻」正義:個人「有義務成為社會生活之積極有益的參與者」,政府則「有責任打造經濟與社會機制,使個人能以其自由與工作尊嚴受尊重的方式貢獻社會」。
書名/成功的反思:混亂世局中,我們必須重新學習的一堂課
作者/邁可.桑德爾 Michael J. Sandel
出版社/先覺
出版日期/2021年2月